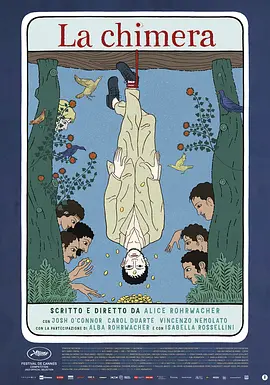怒江 (2023)
怒江 (2023)
怒江 (2023)

导演: 刘娟
编剧: 刘娟
主演: 王砚辉 / 邓恩熙
类型: 剧情 / 犯罪
制片国家/地区: 中国大陆
语言: 汉语普通话
又名: Rage
《怒江》是由刘娟执导,王砚辉、邓恩熙主演的电影。
电影《怒江》剧情简介
最近一段时间,有关80年代的影视考古学,似乎还挺受欢迎的。《怒江:一条丢失的峡谷》(以下简称《怒江》),是80年代的一部记录片,在笔者看来,此片或可重写人们对中国独立记录片史的一些看法。
关于中国的独立纪实,多年以来,人们一直把90年代作为一个分水岭。这是一种传统,虽然经常听说九十年代以前有独立片,但大家都觉得那只是一种巧合,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片,但现在看来,这段历史需要重新梳理一下。
第一次听到《怒江》这个名字,是央视陈晓卿导演(也就是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总导演)和他进行的一次采访,在一次采访中,他提到了自己的早期代表作《龙脊》,也就是1994年的时候。那时候,电视记录片最大的审美,就是以《望长城》为背景,以长镜头、慢动作、慢动作为主,而陈晓卿却要颠覆这种审美,她要用一种蒙太奇的方式,去拍一部新的记录片。这一点,也是从《怒江》中得到了灵感。
“是吕乐和侯咏两个人拍的,这部电影在中国还没有上映,不过我觉得这是一部值得纪念的电影。这部纪录片是用蒙太奇的手法制作而成,遵循了写实的原则,在不影响被摄者的情况下,完整地记录了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,最接近真实的生活状态,没有任何声音,没有任何声音,看完这部纪录片,我很兴奋,因为这对我拍《龙脊》有很大的帮助。等下一次拍《龙脊》的时候,我就想试试。”
在观看《怒江》电影后,作者和吕乐导演进行了一次简短的沟通。在他的叙述中,我了解到了这个记录片的起源与年代。1986年拍摄并于1989年6月编辑完毕的《怒江》是一部以普通电影为尺度的记录片(86分钟)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独立的记录片,比吴文光在1990年所拍摄的《流浪北京》更早,这也是中国独立记录片的开端。因此,中国的独立记录片最早可以回溯到1989或更久以前。
然后,问题又来了,这是一部怎样的纪录片?若有,其在审美、思想表现、生产关系等方面,又具有何等独立、何等开创性?
《怒江》以怒江大峡谷两岸为题材,以四大民族为题材,展现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与民风。35年后再看,就像是回到了过去,在怒江大峡谷里,人们的生活和现在完全不同。80年代中期的生态,依然充斥着原始的气息,依然面对着当年极为简单简陋的时空环境,在这里,他们创造出了应对漫长黑夜的文化方式,那种面对原始天地的人类行为,具有探究天人之中的本质性和启发性。现在,我们在抖音上所见到的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,是非常现代的。因此,重温《怒江》纪录片,可以更好地反映历史与现实的变迁,也可以更好地感受到纪录片保留时间与空间的魅力。
在形式上,《怒江》还是采用了旁白的方式,这也是当时必须要抛弃的记录审美观念,不过《怒江》中旁白所占的比重并不大,而且还采用了采访、提问等方式,让被摄者表达自己对宗教的观点,但更像是一种旁观者的方式。而且,最重要的一点是,这首歌是用同步的。现在看起来很普通,但放在以前,却是非同一般的,要不是这样,陈晓卿也不会被这部电影打动。
电影一开始就以一幅地图为开场白,那就是位于中国西南部边境的怒江大峡谷,那里的地形非常陡峭。视频里,一辆辆轿车正缓慢的在山间小道上行驶着,路面很是泥泞。到了贡山,他们就不能再往前走了,而是租了一匹马,继续往前走。然后,就是在他们深入山谷的时候,他们无意中看到了一幕,一群人抬着一个怀孕的女人,根据他们的描述,这个女人很难生产,被村子里的男人们抬着,带着她向县城的医院赶去。这样的剧情能让人深刻体会到那里的艰难困苦,也能极大地放大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征。
这一开场白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叙述推波助澜,为读者走进怒江大峡谷的人生埋下了一颗悬疑的种子,也为读者的心理埋下了伏笔。他们怎样面对这个艰难的世界呢?怎么才能在如此艰难的生活中维持生计呢?生与死,在这个地方,是那么的不堪一击,他们的灵魂,又有什么可以托付?
本片以怒族为开端,将他们的生活以图景展开,从种土豆、背篓背负肥料、放牛、踏石碾碾米、用石磨削谷壳,从墙后探出头来的孩童,到日出时突然惊起正在晒太阳的老母鸡,再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,再到教堂里的人们唱起歌来。
镜头捕捉到了教堂的每一个细节,小孩的脸,圣像,跪在地上的赤脚,小孩在教堂里奔跑。接下来是面试环节,面试官站在屏幕的外面,而面试官则在镜头前接受提问。第一位面谈者是一位名叫西西里的农民,他说出了这个村庄的信念与精神历史。也有人说起了当地的风俗。接着,这个记录片谈到了土著人最原始的信仰:洞穴崇拜。女人们手持松枝,玉米棒子,围着洞口高歌,怀孕的女人把从石头中渗出的露水往自己头上抹,然后向洞口磕头。记者向记者介绍,多年来,这个原始的信仰与其它宗教,例如拉玛教的教义融合在一起。
接下来,就是九桶村一次怒族的婚礼了。新郎和新娘生活在同村,他们会往天上撒玉米酒,用来驱除妖魔,新郎家会宰了一头牛、一只羊来款待宾客,还有一种加了黄连的荞麦饼,味道有点苦,但是能治痢疾。接着又拍到了村民们聚在一起吃喝的场景,其中有几个场景显示出当地的卫生问题,还有几个镜头也拍到了女人们光着胸脯喂食小孩。
接下来,就是独龙族了。画外音告诉他,在秋收和春种之前,有一种送牛的仪式,是为了感谢老天爷,祈求老天爷赐福,多打猎。村民们首先在贡牛的现场载歌载舞,在醉意朦胧中,他们用镖钉死了一只健壮的黄牛,把牛头割下来,把它的嘴巴塞满了青草,然后把它的脑袋背在身后,又跳又唱,歌词大概意思就是:“牛啊,你是自己吃草的,不是我们杀的,请别怪我们,让我们以后再养牛吧。”
因为很多重要的解说都被限制住了,所以这部纪录片更多的是用镜头来记录当时的情况。摄影机里充斥着人们的谈笑风生,舞动声。在这样的画面中,观众们可以更好地感受到观众们的心情,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比赛的节奏。
那个时候,独龙族只有数千人,而后面的电影里,傈僳族却有十八万七千多人,所以,关于傈僳族的故事,在电影里占据了很大的比例。这本书记录了他们最初居住于四川,1548年为躲避内陆战争而从四川迁移到怒江大峡谷的历史。电影中,他们在盖房子时,采用“换工”的办法,盖了两层,上面一层是人,下面一层是畜生。他们用当地的动物和植物命名,比如蜜蜂,比如熊,比如竹子,比如竹子,比如他们喜欢喝酒。与其多喝点酒,不如少喝点酒,他们要拿出一半的收成来酿造酒。这一段最让人感动之处,就是描写了村民们在夜晚与酒精的联系。由于怒江大裂谷是由北向南的,傈僳族大多居住在裂谷的更深的地方,白天短,晚上长。在一部纪录片中,他们二人共饮玉米酒,并把嘴巴凑在一起,一饮而尽,看起来像是一种亲昵的举动。然后,他们就像喝醉了酒一样,跳起了欢快而自由的舞蹈。电影把两人在一起的氛围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就是静观模式带给我们的好处,解说词并没有将画面的意义完全固定下来,而是保持了其开放性,可以让观众积极地参与到其中并产生情感,很明显,影片更为重视他们生活中的精神层面。
但电影很快就揭露了另一种情况,那就是那些不喝酒,不参加派对的人,他们都是基督徒。记者介绍说,傈僳族以前只有语言,没有书写,很早以前,传教士就是用拉丁字母的倒写方式来创造汉字的。本片以一群人在周末聚在一起,有一次访谈,被问及对宗教的感受时,大家都表示,由于身体不好,所以没有钱去找人去驱邪,重新开始信仰后,一切都迎刃而解。歌舞升平的一幕,衬托出了远处群山中的宁静,深山里的村落房屋,被大火焚烧后,地面上还在冒着青烟,白色的烟雾,红色的花朵,再加上黄昏特有的阳光,给人一种肃穆而美丽的感觉。在这幅画的创造中,明显地包含了作者的一种评论,一种难以察觉的态度。
接下来,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有关“鬼”的故事在这两个家族里展开。这部电影对达友村一户人家的驱魔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记载。巫医根据猪肝上的花纹,就能知道屋子里有没有鬼魂,于是就会跳起舞来,将鬼魂赶走。电影还在继续:法师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驱除妖魔鬼怪,但是一旦人类成为妖魔鬼怪,他们就什么都做不了了。电影结束后,一位名为朵玛的女人被当地的村民称为“鬼婆”,在摄像机面前,她讲述了自己从人到鬼的历程。她的真名叫俅阿海,今年五十出头。
她说:「这我就不清楚了,大约一九五八年左右,有一位妇女前来借来编织的梭子,因喉咙痛,就找了一位女巫来做祭品,结果这位女巫就去世了。大家都叫我 Domma。我自己也很担心,就把那把大砍刀给了他,刚开始的时候,那把大砍刀一点反应都没有,后来我问他来年怎么样,他告诉我,来年会好起来的。可是,所有的村民都不相信,他们就是不相信,为什么我走在他们的前面,他们却要踩着我的脚步,要将我活活的踩死。过了几年,大家都看腻了,就把她定为五保户。”不管你愿不愿意,都一样。”
朵玛也给大家介绍过她的两个老公,一个是一名国民党官员,另一个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男人,一直跟朵玛的爸妈待在一起,动不动就揍她一顿,最后被爸妈给赶走了。在这个故事中,我们可以看到女人的命运,也可以看到社会对个人的压迫。
下一部电影详细地记录了一个村庄的集市。有人带着兽皮,带着草药,带着家禽,带着建筑材料,去市集换取生活必需品,但一般都是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上等的玉米酒上,然后在市集上一饮而尽。尽管市场是一种物质交流的地方,但是这部电影还是把重点放在了农村人的精神生活上。
接下来就是“登梗”澡塘聚会了,这个山谷里的傈僳族人、彝族人,每年春季都会来此享受三天的“洗浴”。男人和女人是分开泡温泉的,镜头里有女人洗澡,但都是偷拍,很多女人都是半裸着上半身,借着树叶和树枝的遮掩,这大概是不可避免的。离澡塘大会不远的地方,就有彝族一支举行“登刀杆”的习俗。电影用了将近15分钟的时间描述了这一仪式,包括他们绕着香案跳舞,把刀系在梯子上,然后把刀放到梯子上,只有少量的解说,说明登刀杆在当地的含义是“上刀山,攀青天,触日月”。英雄们攀上了刀杆,缓缓地攀上了十余米高的刀峰,接着远处的山峦与日出的景象,电影以拉玛尔的颂歌而告终。
30年之后再去看这个电影,我们肯定会把它放到历史的背景下去了解它。在当时的纪实背景中,它的革命意味明显地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电影的解说员只有电影的五分之一,而旁白则是为了提供更多的信息,而不是为了引导剧情。事实上,这样的旁白,完全可以用字幕来表达,让整部电影看起来更加平静,更像是一部“静观”的电影。
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,这个视频有多大的独立性。其独立地位和审美价值,首先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中,其内容和思想品质也是其中之一。吕乐导演为什么会从北京跑到中国西南边境去拍怒江大峡谷呢?从政治与文化的核心地带而来的城市艺术家,在拍摄与叙述中,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层殖民主义的色彩?
在很多年后,吕乐先生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,他说:“这也算是一种文化殖民吧,我们把少数民族简化成电影,甚至是纪录片,他们的生活都很简单,很朴实,而汉人,真的很复杂。”但是,这一次的拍摄,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突然。1982年,吕乐从大四开始就去云南做实习生,与和田壮壮,张建亚,谢晓晶一起拍《红象》,直到1987年上半年为止,其中一年留在内蒙,与侯咏一起拍《猎场札撒》,其余的时间都留在云南,拍了不下两部有关云南及民族题材的影片,其中一部为严浩执导,讲述的是彝族故事(1985年),讲述的是彝族生活。一部年代更久远,是在傣族聚居区拍摄的《净土》,里面有很多少数民族,也有押牛、裸体沐浴等情节,可见《怒江》与这部电影有一定的渊源。因此,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,他不停地对少数民族的生活进行观察,特别是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观察。
在“80后”的第五代文化表现中,有两条线索,但这条线索现在看起来也无关紧要。在一次访谈(吴冠平,一九九六年)中(《摄影师吕乐纪事》,吴冠平),吕乐表示:「我们这个团体,主要分为两大流派,一是以嘉歌、一亦为代表的,以记录中国内地的农民与乡村生活,尝试卸下中国五千年历史的重担;一是以大壮、谢晓晶为代表的,或许因为父母的缘故,刻意回避这些主题,寻求更遥远的地方。“我和侯勇、壮壮三个人,在《红象》这部电影里,我和他们三个人,第一次接触到偏远的民族文化,就是在这里拍的。”
80年代以前的《阿诗玛》,是一种另类的类型,而80年代以后,民族题材和边境故事,却是一种新的类型。部分云南知青(比如陈凯歌《孩子王》的导演,《青春祭》的编剧张曼菱等)在生活经历与创作中融入了云南的边地文化背景,为日后的边地叙事片创造了条件。而《红象》这部由田壮壮带领的剧组,只是碰巧碰上了一位儿童剧制作人。可是当他们来到云南的时候,却被那充满了异国情调的地方给迷住了。就在刚刚,他和吕乐导演交谈时,曾说过一句:
“一九八二年的云南,对我来说,是一个陌生的地方,我们坐了一天的车,从昆明到下关(白族聚居的地方),驻军的哨所,跟古代的哨所一样,都是用土垒起来的,还有塔楼,那时候,文化大革命刚结束,大家都没有出国过,就像是从一个封闭的文化国家,来到了一个充满了原始气息的地方,盈江县有清朝的陵园,英国的铁桥,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摩托车,还有竹子搭建的村落,还有遮天蔽日的榕树,还有田地里的鸟儿,还有一些野鸡,还有一些小动物。”
此后,他又参加了许多以云南为主题的电影拍摄,相比于80年代后期,少数民族纪录片(通常被称作“人类学”纪录片)的逐步崛起,其在故事电影方面的尝试显得更为早期。吕乐的《怒江》是1986年就开始拍摄的,可以说是最早进入这个行业的人。摄像师吕乐在拍摄了《天菩萨》之后,对制片商说,他希望能得到一些资金,自己要做一部记录片。《天菩萨》由深圳影视公司与香港影视公司联合拍摄,并在吕乐的帮助下,获得了一定的投资。
吕乐在民族地区的电影,虽然只是一种工作,但他与“第五代”的电影人,却是一种合作,一种默契,一种自觉,一种主动的精神,尤其是《怒江》的导演,更是一种本能。吕乐导演在与我的交谈中告诉我,他们之所以去边境,实际上就是为了“逃避城市”。但是,在80年代初期,中国还没有成熟的都市文化,所以,她们所要逃离的,实际上就是80年代的主流文化与创作制度对她们的束缚。在另一篇论文中,作者还对90年代兴起的“西藏”、“云南”等一批纪录片导演进行了分析,认为他们并非只是为了寻求新鲜感,更多的是为了在异域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源泉,来缓解自己精神空间的狭小。
《怒江》明显不是在以“工场”为主要内容的“工场”体制下完成的,而“工场”体制又是“工场”体制。因此,我们有必要对该纪实的制作机制进行研究。吕乐毕业后,被分到了一家电影公司,但是因为不习惯电影公司的工作环境,也不习惯电影公司的工作,就被辞退了工资,留在了这里。深圳影视城,与大陆的国有影视城不同,它是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实验田中诞生的,它的股东,是一家香港公司。这家公司想要让吕乐拍一部充满了冒险精神的电影,但是他却选择了一种他觉得合适的方法,而不是按照投资商的要求去做。本片对于怒江大峡谷两岸人民心灵上的关怀,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一种逃离都市文化的本意。因此,这部电影是在他自己的脑海中,也是独立的。
这部电影一共花了五万元,三个月就杀青了,然后经过了剪辑,但投资商看了剪辑,发现剪辑过于偏向“人文”二字,跟他们预想的不一样,也觉得在中国不可能上映,所以就没有再投资音效和后期制作。吕乐在一九八七年年末,前往法国,将这部片子交给在巴黎的欧洲广播公司的一位朋友,后者在深圳、香港等地偿还了贷款,并负责后期制作。此后不久,这部影片在电视上播出,并于一九九○年荣获巴黎国际人类学影展最佳影片奖。
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,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没有在传统的制片模式和老的国有制度下生存,事实上,它也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创作制度, ARTE虽然也是一种制度,但是它只是辅助后期的工作,而且与导演在创作理念上也比较契合,所以才能很好地合作。从审美角度来看,由于该纪录片是作者自己提出的概念,并不是为某一平台量身定做的,在此过程中,又机缘巧合地拿到了必要的经费,因此,创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已有的审美素养,自然而然地将其拍摄下来,从而在影片语言上取得了重大突破。但是,在那个时候,这个审美上的突破,并不只是导演本身的审美积累,八○年代的电视纪实工作者,很早就意识到了同时播放与删去遮蔽画面的解说词的重要意义,只是碍于旧的工作制度与技术,一直没有实现的机会。
陈晓卿导演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灵感,是因为她将自己与《望长城》中的某些电影进行了对比,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。尽管《怒江》并未有意使用长镜头来叙述,那是80、90年代中国影视工作者“择善固执”的一种表现,但它仍是一种较为冷静的观影方式。正如前面所说,虽然有旁白,但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,只起到了一个信息的作用。这样安静地看着,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,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,这在当时,也是一种开创性的独立记录片。尽管《怒江》的风格比较自由,比较杂乱,但是它还是充满了一种宁静,因此它也是一种革命的审美趋势。
诚然,在影片的创造过程中,我们可以说带有殖民主义色彩,但那不是主要原因。你会发现,他们并没有那么新奇,就像投资商们认为这不是一部稀奇古怪的电影一样,他们只是把电影当成了一条主线,更多地关注了当地人民的精神生活。你能感觉到,在静观电影的倾向性下,观赏者的沉迷,以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融,这是一种对人类精神线索的渴求与耐心的追寻。它的作家特征也体现在这一方面。
这类对边地少数民族原始的视觉素材的直接剪切,它所具有的多样性与模糊性,在那个时代的传媒中是较为难以接受的。无论从电影的制作机制,还是从电影的传播机制,亦或是从电影的艺术风格与观念上来看,都是一部具有自主性的纪实作品。
但问题是,这部纪录片是否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独立记录片?多年来,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起步于吴文光的《流浪北京》,但我在2016年石家庄参加一个研讨会时,曾听温普林说,从时间上看,他的《大地震》是80年代最早的一部纪录片。然而,《大地震》一书已失传,无从寻觅。这个记录片只是一个剪辑版吗?有没有在什么地方上映?这一切,都需要时间去验证。《怒江》是迄今为止有证据有证据的第一个独立记录片,根据吕乐的记忆,他的后期制作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。在没有新素材的情况下,《怒江,一条丢失的峡谷》将成为中国的第一部独立纪录片,而《流浪北京》只比它晚了一年,所以,这一点对独立纪录片的起源有什么意义吗?或许不是很重要,但是,我们可以把一部已经被遗忘的影片,重新写入电影史,成为中国电影史、特别是独立电影史的一个新的参照点。
拍摄过程
2022年3月,电影《怒江》在云南腾冲举行了开机仪式。
演职员表
演员表
演员

王砚辉

邓恩熙
职员表
职位
姓名
总制片人
蒋浩
导演
刘娟
监制
贾樟柯
编剧
刘娟